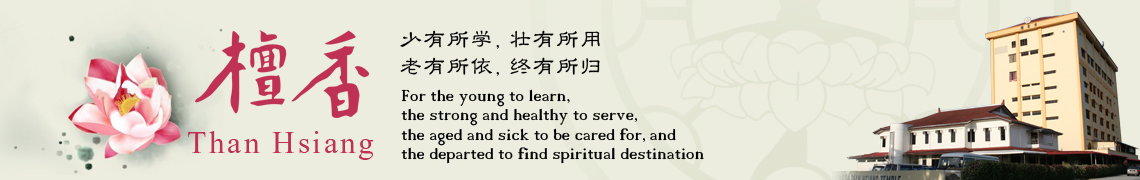想不到,此生竟有机会与温州结缘了。在我原本的印象中,这里只是行走天下的商人的故乡,怎知道它又是一片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崛起中国人脊梁的皇天厚土呢!
缘起
起因是一场足以吓死人的病。本市搞两癌筛查,我被选中参加,并有幸“中了头彩”,被查出我那随身携带十几年的乳腺肿块乃属“可能恶性发现”。历经三家医院,做了一次钼靶和两次彩超,B超大夫直接给我定了性,径直说是癌了,门诊大夫也说是八九不离十,要做了穿刺活检后才能定性。震惊,痛苦,哭泣,惶惶不可终日。但细想也在情理之中,这十几二十年活得并不舒心,工作紧张焦虑,家中时有争吵,自己心思繁杂,脾气暴躁又压抑,生活极不规律,因一胎化所限曾经流产数次,罪孽深重,又胡吃海塞,时常饮酒买醉,不爱运动,便秘失眠,体重超标,又焉得不病?医生断言,能不能保乳还要看,但化疗是逃不掉的。周围朋友纷纷相劝,是可以治的,很多人切除就没事了,快点做掉吧!天哪,切除,化疗,真的到了这一步了吗?我的一位同学不久前与我相见,她在近十年前已有此遭遇,已经办了残疾人证,至今仍在吃药,大热天穿得很厚,怕累,怕冷,饭量小得很,我见犹怜。难道,我的此生也要这样交待了不成?
情急之下,我开始上网紧急搜索一位老先生,一位旷世独立的民间老中医,他就是行医五十多年、名闻遐迩的温州奇人潘德孚先生。危急时候,信息储备帮上了忙。一段时间以前,我就在网上拜读过老先生的大作《天下无癌论》,当时就感觉仿佛开启了一扇窗,看到了一片被遮蔽的天空,对他的观点和论证深为信服,但因觉得这事距离自己尚远,没有特别关注。现在不同了,事关生死,老先生将是我治病生存的救星。我疯狂地去网上,搜索老先生的博客文章,把他在草根网的博客文章一篇篇打开阅读,从中查到了先生的电子邮件和电话号码。我流着眼泪,给先生写了邮件,讲述了自己的个人情况和患病始末,请求他救救我。先生当天就迅速回复,语气坚定地嘱我来温看病,并告知了地址。我又询问出诊时间,先生再度立即回复了。
心情好受了一些,但到了夜里又有反复,感觉陷入绝望的深渊,便又爬起来,上网看先生在北大医学部的讲座视频“老潘说癌”,前后看了两遍。在先生的讲述中,现代医学对癌症的认知和治疗体制犹如一座脆弱的沙盘,略经拆解就轰然倒塌。先生不是小说家胜似小说家,用语非常生动,带着泥土的质朴和草根的豪迈。他极其擅长处理概念,创造性地提出“生命是信息运行的一个自组织的过程”,严格把生命和身体区分开来,指出“是生命生病,不是身体生病”,极大地强调了生命的自愈能力,认为只要生命还在,就会焕发出强大的自愈生机,医生只是给病人帮帮忙,帮助他启动自愈力而已。西医靠着解剖尸体来治疗活人,何异于刻舟求剑,而且医生把病人放到被动承受的位置,其实是本末倒置了。他巧妙地化用冯小刚的电影《天下无贼》,提出了惊世骇俗的“天下无癌”理论,以大无畏的战斗精神,对西医的癌症之说展开了火力超强的批判,指出西医弄出所谓癌细胞、转移、扩散、得癌必死之类的假说,既是为了扩大市场,也是为了推卸责任,其后果不是把病人吓死,就是把病人治死,对于极少数劫后余生的幸运者,则包揽为自己的功劳。先生直言,自己不会治癌,只会治肿块,方法是见招拆招,辨证治疗,只要把症状治好就行,不必纠结于病名是什么。“肿块”一词,带给人的威慑和震撼就小多了。“肿”,皮肉浮胀,月到中天,圆圆满满,块,疙瘩或团,这听起来很家常的两个字,对于病人来说,该是多么大的心理慰藉!
先生还惯用形象的比喻把复杂的机理解释得通俗易懂。他形容生命是一条河流,从高山发源,最后汇入大海,中途偶有泥沙瘀积,但通过水土保持可以清瘀,或者可以绕道而行,照样东归大海,完成天年。西医不去治理上游的水土流失,反倒纠结于瘀泥的构成,机械地挖掉瘀泥,留下一个坑,水要是流到坑里,就到不了大海啦。他形容经络是信息的通道,是一种关系存在,好比父子之间的关系,虽看不见摸不着,但却十分重要,比如,父亲穿儿子买的鞋子就不用付钱。他主张“是药三分毒”,为免毒性害人,治病要适度,治到七八分就让病人自己恢复,好比行船,离岸200米时就关了发动机,让船凭着惯性自行靠岸。凡此种种令人听了如沐春风,豁然开朗。在这段视频下方的评论中,有人评了六个字“中国人的脊梁!”性情中人的我见此非常激动,不禁流下热泪。是啊,先生这样的实践探索者和理论开创者不仅是中医的脊梁,更是中国人的脊梁。正是有了脊梁的坚强支撑,我中华民族才几千年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如今西医一统天下,中医势微之极,但有先生这样孜孜不倦为中医鼓与呼的斗士,相信中国人将越来越多地从崇洋媚外的迷梦中苏醒,中医不久将迎来复兴的那一天!
我决定,扛住朋友家人催促去医院做手术的压力,到温州去,找潘老先生。
成行
怀着前途未卜、忐忑不安的心情,囊中带着刚买的先生所著《解悟中医——相信你的自愈力》,清晨登机,踏上了生来最远途的求医之旅。机上不时闷睡过去,醒来就读书,读到先生书中“乳房小叶增生治疗体会”一节,其中有位女孩仅仅因为小叶增生就做了乳房切除术,而另一位幸运儿遇到潘先生,仅靠疏肝理气的中药就恢复如初,免除了切肤之痛,不禁深感现代医学害人非浅,而我这一趟应是找对人了。顺便提一下,先生书中写的病案都非常生动,有背景有人物有情节有对话,风格读来颇似古人的笔记小说。
午后时分,在温州市区繁华地带的一条幽深的小巷,我终于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潘先生,惶恐纠结的心理此时得到释放,不禁润湿了眼眶。先生跟视频当中一样,坐如钟,声音也如洪钟,非常有精气神,看上去也就六十多岁,操一口南方口音的普通话。听我说到此前已经看过先生的著作和视频,对他的思想理念有所了解,先生便先谈了一些自己的医疗观念,指出西方医学对生命没有研究,只会制造紧张,肿块不会导致死亡,只有整个生命系统的毁坏才会引发死亡,并批评了现代医学的病因单一化、治疗划一化、责任集体化、组织上政医一体化诸多弊端,指出医院是集体责任制,一环套一环,其实意味着谁都不对病人负责,而他这里病人跟医生是一对一的,他会对我负责。然后,先生查看了我带去的片子,仔细询问了我的病情、生活起居,还把了脉,看了舌苔。先生问我有没有做穿刺活检,我说没有,先生连声说好,说根本没必要去穿刺查证肿块的性质,毕竟有肿块总是要治的。先生认为治病最重要的还是心理,嘱我心放宽了,不要怕,但要好好治疗,以后不要再吃西药了。我是下午第一个来看病的,随后进来的是一个妈妈带着小女孩,我怕她们着急,就请先生给她们先看,不料先生说,我的情况已经快看好了,并给我开了草药。原来我视若大敌的病症,在先生看来不过寻常,他此前早已治愈过好多例。看病之余,我还得到了先生新出的一套五本的宏篇巨著,分别是《西医病理百年反思》、《医学理念》、《人体生命医学纲要》、《治病的常识》、《铁杆中医宣言与现代医学批判》,先生的思想理念尽收其中。我打算把它们带回去好好研读,并认定它们就是我的护身符。
我拿到草药的时候,有一位中年妇女带着家人来看病,原来她本人也患有跟我一样的病,已经吃了半年的药。她一个劲儿地安慰我说,这个病没事,并教给我熬药的方法。我看她神情泰然,满面笑容,想必生活质量非常好。先生的儿子这时也在场,温文尔雅,家学深厚,此时也对我说,这只不过是个慢性病,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向大家求证,是否仍觉得生病的我还是个正常人?先生的儿子笑道,本来就是个正常人嘛!原来先生的儿子业余跟先生学习中医,经常过来帮忙,也是颇通医理的。看来我此行的看病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对先生说,原本还以为要在温州住一阵子慢慢治病呢,先生笑着说,住下来好啊,可以在温州好好玩一玩了,至于治病是不必住下来的。
诊所里人渐渐多起来,来来往往,络绎不绝,但大多讲的是温州话,我听不太懂。印象最深的是有两个女孩,其中一位脖颈酸痛,不能动弹。先生用几根银针给她扎了一会儿,就立即好转了,她连呼“这简直太恐怖了”,其实她是想表达“太神奇了”的意思。她跟先生聊了好一会儿,描述她的各种病证,先生不厌其烦地跟她分析,还怪她此前轻率地在医院把子宫切除了。这与先生的医疗理念是相符的,生命只有作为一个整体,才能正常发挥神奇的自愈力,怎能轻易去除任何局部!过了良久,我才跟先生告辞,先生嘱我走好,在温州好好玩一下。
这次来温州机会实在难得,我觉得还应当到先生的诊所去感悟一下,好进一步增强自己的信心。于是,第二天上午,我又鼓起勇气,来到诊所看先生诊病了。八点多钟的光景,诊所里里外外都是人,问诊者一个接一个。我跟先生打了个招呼,便站着看他诊病,过了好一会儿,才得到个空位坐下来。旁边一个从台州来的女孩,带着父母来看病的,父亲因腿部肿块去求医,却查出肝部肿块,辗转北上石家庄,那里的医院却不能医治,后经多方查找,才来到潘先生这里,这是第一次来。先生指示一位助手,用针扎进女孩父亲的膝盖肿胀边缘部位,再把针拔出,污血猛地涌出来,人变得精神些了。女孩的母亲腿脚也有不适,也是照此治疗。过了好一会儿,女孩扶着父母慢慢离去了。真是个孝顺的女儿,相信在潘先生医治下,她的父母会很快好起来。
接下来,身边又坐了一位温州当地的女士,言说身患肾衰竭,已经九年了,西医救不了她,主张让她做血透,她抵制住了。也曾北上大连数次,但也不得其法。不料近来找到了潘先生,吃了先生开的药,如今是第二次来看,已经大有好转了。我看她气色非常好,不像是个病人。她镇定自若地告诉我,已经多年不看西医了。她一再对潘先生表示感谢,说想不到家门口居然找到这样一位名医。她还说,自己一直抱定一个不会死的信念,现在果然好转了。看来,除了潘先生妙手回春之外,病人的自信心也是至关重要的。这一次,看到先生不停地忙碌,我在诊所停留的时间比较短,很快告辞了。离开时,先生嘱我“一定要有信心”。
回到旅店,想到这两天在潘先生诊所的亲切体验,我不禁回忆起自己以往与现代医学打过的交道,颇有不堪回首之感。记得怀孕期做例行检查时,医生曾拿我额外试验一种新药,还要我自己买单,我竟傻乎乎地同意了,还好,孩子一切正常。生产的时候,我在待产室长时间地震痛,不得要领,毫无进展,但没有哪位医生护士给我过一点辅助和一句指导,更别提安抚了,反而因为叫喊而批评我。最后看我实在生不下来,干脆送上手术台实行了剖腹产,肚子从此变成高低两个平面,总是紧绷绷地不舒服。我因右上腹偶痛去求医,开了各种检查单,各科查了又查找不准部位,最后给我开了胃镜,经过痛苦的胃管穿喉,得出个浅表性胃炎的结论了事,至今问题仍未解决,右腹仍会偶痛,现在我明白乃是肝郁气滞所致,但西医是不问原因的。后来做流产时,医生竟开单让我去拍X光胸片,说规定半年内没拍过就得拍,真搞不懂流产跟胸片有何关联,利益而已。我做过阑尾切除术,落下一个挺长的口子,术后恢复不好,留下了附件炎这样的后遗症。我犯了牙痛去医院,医生说这是智齿,得拔掉。我不知什么是智齿,只知这是我最靠里边的一颗大牙。当时痛得未加考虑,拔掉了,后悔啊,我的口腔右下方从此变成了一片永远不能填补的虚空,导致上牙下沉,脸形恐怕都要变了。就这样,连割阑尾带拔牙,西医在我身上已经做了两次减法,我不禁想问,难道西医的大道就是“至减”不成?。这一次,如果不是我找到潘先生,再做一次减法是免不了的。
在潘先生的诊所,我仿佛找到了久违了的童年乡居的感觉。那时候,我们全家住在村子里,邻里往来频繁,关系温馨融洽,晚间没什么娱乐,最好的享受就是串门儿,亲朋邻里聚在一起聊天,聊到很晚也不愿离去。谁有难处大家都愿帮忙,相互周济是常有的事,母亲还曾成功地给邻居做大媒。先生的诊所也是如此,大门开放,不用挂号,可直接上门就医,就像探亲访友。人多时就在旁边等会儿,或看先生诊病,或跟病友聊聊天,交流一下病情和治疗心得,相互鼓励,再时不时插话问先生一个问题。在这样的氛围里,求医者心情放松,极易跟医生建立信任,也容易树立治疗的信心。有了信任和信心,治好就有了一半的希望。
我生性胆怯,不善交往和走动,但因在先生的诊所感到了难得的轻松和亲切,第三天早上,又忍不住三度来到这里。不料这一次,我竟然碰上难得的机缘,有幸跟先生畅谈了整整一个上午。我到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已经在找先生问诊了,他们谈的是温州话,我不大听得懂。大概他身体没什么大问题,先生没有给他开药,连诊费都没有收。年轻人爱好中医,有意自学,故而准备了好些问题向先生请教。两人聊着聊着,大概是为了照顾一旁的我,便特意转成了普通话,我就逐渐加入到讨论当中。由于诊所今天病人较少,我们抓住时机提出各种想问的问题。三个人,你一言,我一语,我们提问,先生作答。我想进一步增加治疗信心,便问先生觉得我气色怎样,先生给了我响当当的三个字“非常好!”闻此,我算是吃了一颗定心丸。我又问先生,可否多开一些药让我带回去,先生很负责任地告诉我,要先吃完这些,看看效果,再议药方和开药。关于如何看待父母的病痛,先生主张,要尽量顺从老人的心情和意见,老人有点小病小痛,只要不影响基本生活,做子女的不必太执意逼他们去看医生,以免双方都背上思想负担。我说起父亲因冠心病做了心脏支架,先生为这样的治疗感到遗憾,但提示我不要告诉父亲上了支架不好。这表明,先生的一贯原则是照顾病人的心理感受。
潘先生注重概念,正考虑用一个新的概念来替换癌症,因为癌症这个概念是西方人的发明,就像艾滋病一样,属于无中生有,吓人蒙事的。我向先生求证,癌细胞是否真的会转移和扩散。先生直言,这个说法难以查证,做不得准,癌的变化只是想象,不是真的。接着又振聋发聩地指出,现代医学整个是一个骗子,而且已经精怪化。比如像疫苗这样的东西,没有任何好处和必要,给孩子打了,只会让身体变差。闻此,我打算以后不让孩子在学校再接种疫苗了。我说话当中念了错别字,把“灸”念成了“炙”,先生指正我说,“久火为灸,月火为炙。”先生有一个心愿,希望自己有机会到海外去讲学,把他的理念传播出去,只是苦于不懂英语。我对先生说,不需要懂英语,因为海外华人太多了。后来,我才又从别的书里看到,外国人根本不相信说英语的中医,只相信不懂英语的中医,认为这才是真中医。在场的那位年轻人询问,可否到先生这里来学中医诊病,先生爽快地同意了,欢迎他过来看看。记得先生曾遗憾已故治癌大师郑文友对其药方秘而不宣,没能继续遗泽后人,此次眼见先生对前来求学的人都持欢迎态度,还对我说,要是我下次来温州住下,每天到诊所看他治病,看上三个月,就能写一本书了。
我认为先生是个爱国者,但先生却不认同,而是表示,如果说到爱什么的话,“我爱我的民族。”国家和民族的区分透露出,先生对权力避而远之,只愿融入普通民众当中,做点踏踏实实的事情。我想起,先生在自己创建的早叫庐网站上,自比为一只早起鸣叫的公鸡,虽然惹的沉睡的人们纷纷埋怨,照样矢志不渝地履行预警职责,尽早唤醒梦中人。是啊,如果叫醒更多的人,让他们知道天下本无癌,庸人自扰之,就可以帮助他们逃掉伤身、劳民又伤财的惨痛命运了。谈话到最后,先生见我是学文科的,就送给我两本他所著的医学之外的书,即《语文学林改错》和《汉字编码设计学》,这是先生深入涉猎的又一大主题领域。这一趟温州之行真是来得太值得了,既得到了救治,又长了见识。告别时,我对先生说,真是胜读十年书啊!
归来
我带着潘先生开的草药和他的著作,轻松愉快地登上了回程的班机,跟来的时候心情完全不同了。在机上,我没再看医疗书,改看先生送我的语言学和汉字编码著作。一看才恍然大悟,原来我用五笔字型打字这么多年,还是有许多字打不出来,要改用拼音,这不是因为我太笨,而是由于这种编码太复杂太难记。可笑这么多年,我竟不知除王码五笔之外,还有别的输入法。先生的领地远不止于此,还触及到汉字的改革、学校的教育等重大话题,处处散发着迥异于所谓主流专家教授的真知卓见光芒。他反对汉字拼音化和拉丁字母化,反对学校过于看重英语学习,这都与他坚守中医、反对数典忘祖是相通的。当前语言文字领域的自我殖民化极其严重,先生的振臂疾呼正当其时。原来,大凡专才奇才,必是博学之士,一个好的老中医不止是一座好的医院,还是一本好的百科全书。
短短几天的温州之行,我已经喜欢上了这个地方。除在潘先生那里的收获之外,我还难忘美丽浩荡的瓯江和孤悬江中的江心屿,还有朱自清故居铭刻的那些写在温州的美妙散文,占据中华戏曲四分之一江山的南戏,我买了温州鼓词和瓯剧影碟带回来欣赏。在华盖山公园,有位精通摄影的老者主动上前帮我拍照,让我留下了构图绝佳的留影。在中山公园,几位民间书法家热情地蘸水挥毫,在地上写下我念出的唐诗,供我摄取留念。在府前街,几位老者搭起免费的茶摊,供路人解渴,这是我在别的地方从未遇见过的温暖风景。长人馄饨真是好滋味,连吃好几天都不厌倦。遇到的每一个当地人都是心平气和,温文尔雅,颇有文化底蕴,让在粗粗拉拉氛围下生活的我感到耳目一新,十分惬意。雁荡山和楠溪江是向往已久的,此次行程匆匆未及前往,留到下次吧。温州,我还会再来的。
近年的我随着年龄渐长,开始回归中华传统文化,偶然喜欢拼凑一些不合格律的近体诗。对这次温州之行,我也在诸多感触之下,凑成了这样一首:
缘来温州行,绝处又逢生。
赤日灸痛减,瓯水洗瘀清。
后巷明辨证,前途罢刀兵。
仙人授瑶草,将以致泰平。
回来的第二天,我就开始吃潘先生开的中草药了。吃下去感觉浑身热热乎乎,神清气爽,尤其肿块部位有一种灸治的感觉,非常顺畅舒服。吃过几天之后,我渐渐体味到,自己恢复成了一个草木之人,重新建立了与自然、与土地的联系,通体舒泰,排便顺利,右上腹的隐痛渐渐得到缓解,整体健康状况比病前好多了。我甚至有时感觉肿块变小了,但还不敢确认,怕是错觉或心理作用使然。但转念又一想,这样的心理作用无疑是好的,心病还需心药治。我老公的想法跟我不一样,原本倾向于主流疗法,他去信给潘先生表示了疑虑。先生百忙中回复,一针见血地指出,医疗选择有时候是生与死的选择,选择错了,就等于把人送到屠刀之下。
回京一个月后,适逢潘先生来京回差,我有幸再次拜会了先生。我参加了先生在京所做的讲座,见到了先生在京的众多粉丝,气氛之热烈让我很受鼓舞,深感先生之道不孤也。先生的儿子陪同前来,我又有幸跟这位青年才俊聊了一会儿,感觉他与先生的思想一脉相承,言谈也带有先生的犀利之风。他除了向我着重申明活检穿刺的危害,还说了一句话令我至今印象深刻,“看不见的东西,不要以为它不存在。”这话当时让我感觉像是奇谈,但到后来,我读了许多道家的书,比如熊春锦、南怀瑾等先生的著作,就深感此言非虚了。世界原本是由“有”和“无”组成的,“无”是“有”的源头,太极黑境里蕴含着祖先早已知道、现代人却置若罔闻的生命本源。
此次讲座中,先生抨击了现代医学的种种精怪化弊端和巨大危害,还特地指出,生气就会生病,女人尤其要胸怀宽大,肚量不生气,多想想老公的好,想想把孩子养大有多好。先生虽未指名,但我知道,这话是专门针对我而说的,心里十分感动。我想请先生再复诊一下,就于次日清晨带老公一道,去了先生下榻的酒店拜访。一大早赶过去,先生顾不上吃早饭,跟我们谈了半个多小时,重点是打消老公的疑虑。当老公表示我们其实有医保、在医院看病能报销时,先生当即指出,“医保是保医的!”这句话我后来反复回味,振聋发聩啊!先生还给我号了脉,看了舌胎,修改了药方,嘱我饮食清淡些,而且不收我的诊费。告别时,我对先生说:“还要麻烦您做家属的思想工作,太感谢了!”先生却说,他看病都是希望家属一起前来的,这是他治疗的一部分。过了几天,先生特意发来邮件资料,嘱我改吃素食。由此,我才走上了全素食的道路。
我继续读潘先生的著作,并按图索骥,根据潘先生书中提到的一些书名,开始了广泛的阅读。我购买了许多现代医疗批判作品以及中医如何看待和治疗疑难大病的书籍,有中国的老中医写的,也有外国的顺势疗法、印度医学专家写的。越看,就越有信心,越感到自己走对了路子。很多中医仍对现代医疗抱有一定幻想,甘居从属地位,会建议病人先到医院做手术,再由中医上手调理,惟有潘先生对现代医疗的批判最彻底最有战斗力,对中医的捍卫最坚决最有防御力,一篇《天下无癌论》打了一场漂亮的防守反攻,全盘端掉了西医治疗癌症的根基,带给病人最大程度的乐观和信心。通过潘先生等人的著作,我已经成为了一名中医爱好者,打算多了解一点中医理论和常识了,既是为了自己治病和强身健体,也可以呵护家人健康。
随着时日的推移,我越发深切地体会到,当日是潘先生为我挡住了屠刀,开启了生命自愈之门,展现了一片从未企及的生命新天地。如果不是这样,我的状况是难以想象的,最好也就像我那位同学一样吧。先生的著作为我竖起了牢固的心理屏障,先生的草药为我打下了良好的治疗基础。后来,我由于想尝试自然疗法,未跟先生商量,竟自作主张不再服药了。我因此对先生一直心存歉意,但先生并不介意,仍然关注着我的情况进展,时常发来邮件,提供最新撰写的研究论文。其实,我深深知道,我从未停止服用先生的药,这些文章就是先生开出的心药,是一粒粒定心丸,让我时而摇摆的心理很快恢复平静,沿着自己的路坚定走下去。
记得我看到潘先生诊所的墙上挂着书法写成的两句诗,很感兴趣,但因孤陋,未能逐字辨识清楚,经先生颂读,才知是“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上网一查,是前贤顾炎武诗作中的两句,寓意人到暮年,犹壮心不已,耕作不辍,用来形容潘先生自是十分贴切。另有别人赠送的一幅字,写的是“敢为天下先”,足以说明先生先天下之忧而忧、为人之所不敢为的启蒙大众之功。我竟突发奇想,要借用这几句缀成一首七律,专门描写潘先生其人其事了。于是,就抖胆续貂,有了下面这首:
先生奇人出永嘉,半世厚积今薄发。
义胆仁心先天下,笔耕口授闻迩遐。
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
早唱雄鸡惊迷梦,不教屠刀滥砍伐。
(注:半世:半个世纪。迷梦:世人对西医的执迷不悟。早唱雄鸡:先生自比为早叫庐的公鸡。屠刀:西医对抗疗法)
先生年近八旬,这个年龄对于普通人来说,自然是“苍龙日暮”、“老树春深”。但对于一位妙手仁心的名老中医来说,却是龙驭九天、树大根深的黄金时代。先生的工作量是惊人的,每天看诊全国各地的大量病人,处方、拿药、制药、改方、寄药,接受病人和家属问询,其余时间笔耕不辍,不几天便有一篇新作问世,以飨病人、同行和读者。这些文章把握医界动态,切中时弊,为疲弊势微的中医和不知所措的病人撑起一片独有的天空。近日更获悉先生即将向医学社会学新领域进发,令人感佩不已。潘先生的辛勤工作是中医和病人的福祉,衷心祝愿先生健康长寿,把“天下无癌”理论以及他在多个领域的诸多创见进一步发扬光大,造福国人,进而传播四海,造福世界。
感想
温州之行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又是获得重生的起点。此前一、二十年的生活充满了痛苦和纠结,终至沉入谷底。从温州开始,生活不再是工作挣钱这条单行线,心境变得松驰起来,状态开始从谷底攀升。我试着回归生活的本源,在得了病以后,反而品尝到一丝久违的甘甜。有时候,我会庆幸自己被查出了癌症,让我有机会停下来,静下来,反省前半生的纠结痛苦,忏悔以往的错误和罪孽,改变心境和生活方式,阅读、走路、节食、饮水、听音乐,坐看四季变更和人事变迁,成为生活的旁观者,变得宽容平和起来。医保不重要,自己才是保障,这样一想,生活的压力和负担轻多了。老子说,“馀食赘行”,人用不着吃太多东西,就能活下去,吃多了反而得病。人们疲于奔命地工作挣钱,无非为了多占有些物质,多占有就是多浪费。温饱足养人,致富不光荣。少一点物欲,就能多一点自在,也给子孙后代多留点存活空间。
我年轻的时候活得昏昏噩噩,妄自菲薄,一度恼恨自己生为中国人。但四十岁以后,我仿佛找到了主心骨,越来越爱自己的祖国。王凤仪性理讲病学说传人刘有生先生说过,生在中华是三生有幸的事。此次生病,让我更加庆幸自己生在中国,可以得到五千年传统文化、儒释道三教学说的滋养。无名氏在《内证观察笔记》中说,“疾病是认识和寻找真理的捷径”,“只有你自己所属的文明,才能拯救你自己。”老子说,“吾欲独异于人,而贵食母。”是啊,回归自身文化的本源,才是养生治病的正道。中医,正是中华传统文化桂冠上的明珠,当外国人都越来越多看中医、掀起中医热的时候,置身中华本土的国人,却一窝风地去求救于仅为末学的对抗疗法,恰好应了潘先生所说的“自毁”,实在愧对先人。这是一个扭曲的时代,“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中医的希望在民间,中国的希望在民间,因为中国人的脊梁向来出于民间。
我对主流治癌看得比较透了,没再去过医院,对复查敬而远之。心情已经从最初的震撼中平复,逐渐不再拿这病当回事儿,担忧和烦恼的时候越来越少了。在此期间,凡是简便易行的自然疗法,我都愿意尝试,坚持到现在的主要有素食和尿疗。身体状况良好,肿块还在那里,安然无恙,像个伙伴与我朝夕相处,又像个忠诚卫士防御着积毒的侵袭。老子说,“圣人被褐而怀玉”,我想,不妨学习圣人,把肿块当作怀藏的玉石来珍惜吧。要是有一天它消失了,恐怕我还会失落呢。
潘先生的名片很大,上面印有60条医学理念,我把它装进相框,放在案头,时时观读,心里感觉很踏实。前路漫漫,先生的思想理论将继续庇护我前行。先生新近指出,人的核心是意识系统,西医把癌症定性为必死的病,就等于摧毁了人的意识,让人失去生机和勇气,所以总能自圆其说,印证其论断的正确性。反之,乐观的心态,加上饮食、环境、生活方式的调理,却能让人激发自愈力,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我时常在网上关注作家布里亚特的言论,尿疗就是受了他的影响。老布与庄则栋先生同时查出癌症,老布是膀胱癌,庄先生是直肠癌,由于选择的道路不同,五年后,庄先生于春节时不幸离去了,老布活得好好的,到处游山玩水,开导病友,影响了一批人。
湖北卫视有个《大王小王》栏目,关注弱势群体,为普通人排忧解难,在娱乐至死的电视丛林中,实属难能可贵。这个栏目经常邀请一些重症病人作客,有癌症、白血病、尿毒症、心脏病等,听他们讲述治病的巨额花费和生活的艰难,为他们送上一点善款,并发动观众为他们捐款治病,帮他们开网店自食其力。用意非常好,连同微博上的一些捐款救助呼吁,都是出于博爱,但都忽视了一个关键点:治疗对路吗?捐款是在帮人治病,还是在给医院敛财?有一次,看到一位白血病患者父亲境况悲惨,我因读过潘先生所写的《白血病人将获救序言读后》一文,购到了孙起元先生的原著,对此病的治疗有所了解,便忍不住想帮忙的冲动,在网上跟人家取得联系,推荐中医治疗,但还没说几句,人家却回复说,别再给我发这样的东西行吗,我很忙!对此,我只能一声叹息。原来,经验是不可传授的,中医需要缘份,人只能走各自的路。
见到我的现状,有人说我这不是癌症,何况又未经确诊。这真是个怪圈,没事就说不是,是了又治不好。直径三、四厘米,坚硬如岩石,表面核桃般高低不平,怎么说都在这病的定义范畴内,我仍记得两家医院言之凿凿的断言,基本上认定了。如果没事,只能说明西医的绝症定义有问题。潘先生说,癌症是西医的发明,扩散、转移、恶性、分期都是假说,目的是开拓市场。威廉•恩道尔在《目标中国》一书中说,中国引进西医,等于引进了一场阴谋。老布说,癌症是思想病。安德烈•莫里兹干脆说,癌症不是病。正是:
癌症不是病,未必要人命。
纷纷世人迷,视之为恶性。
状若临死地,惶惶无宁静。
除之而后快,竟相干戈动。
茱莉切胸后,媒体齐称颂。
道是真勇敢,市场更兴盛。
对抗三板斧,苦难无底洞。
医院财源广,病家独伤痛。
人去钱花光,终究一场梦。
临渊须警醒,退步寻蹊径。
潘公如椽笔,发聩启懵懂。
癌字古已有,肿块岩石硬。
气滞血瘀积,病根自家种。
患在生命体,割肉不管用。
信息自组织,痊愈待时令。
环境心境改,块垒可平定。
治本不伤人,中医何殊胜。
传承五千年,民间有呼应。
迷津潘公指,悟者足称幸。
庸人徒自扰,天下无癌症。